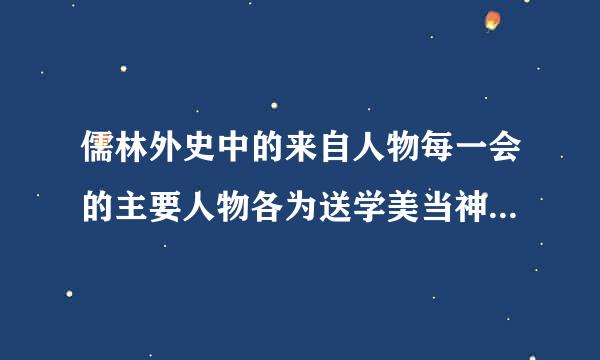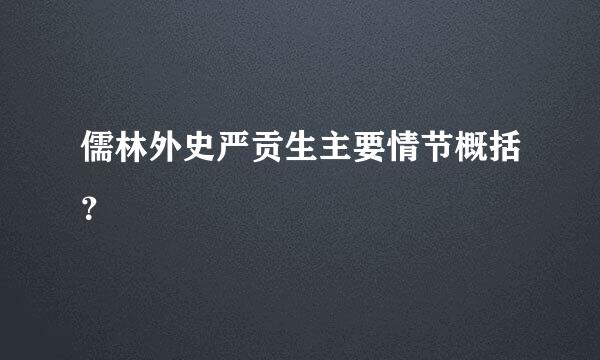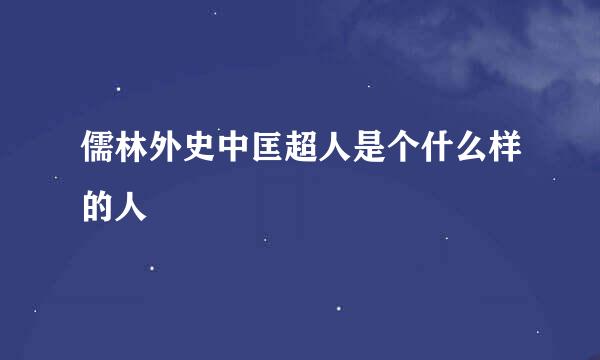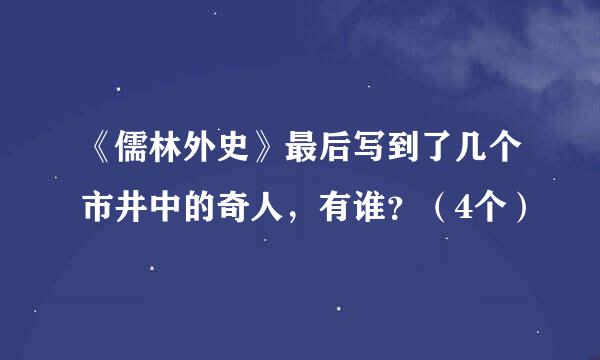
第一个是会写字的,这人叫季遐年,自小儿天家无业,总在寺院里安身。每天跟着和尚在寺院里吃斋,和尚倒也不厌他。一个会写字的人到底奇在何处?奇就奇在他字写的好却有很多的怪癖和举动:“他的字写的最好,却又不肯学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创出来的格调,由着笔性写了去,但凡人要请纸不田区限南处扬给他写字时,他三日前,就要斋戒一日,第二日磨一天的墨,却又不许别人替磨。就是写个十四字的对联,也要用墨半碗。用的笔,都是那人家用坏了不要的,他才用。到写字的时候,要三四个人替他拂着纸,他才写。一些拂的不好,他就要骂、要打。却是要等他情愿,他才高兴。他若不情愿时,任你王侯将相,大捧的银子送他,他正眼儿也不看。他又不修边幅,穿着一件稀烂的直裰,靶着一双核料宪讲无破不过的蒲鞋。每日写了字,得了人家的笔资,自家吃了饭,剩下的钱就不要了,随便不相识的穷人,就送了他。”他到一个朋友家去,一双蒲鞋沾了好多泥,拿人家想办法让他换鞋,他来气了,没有进门而且一顿挖苦:“你家甚么要紧的地方!我这双鞋就不可以坐在你家?我坐在你家,还要算抬举你。”施御史的孙子来担张粮段万茶功半且知请他去写字,他对他们的怠慢不高兴,不高兴不来自去也就罢了,可是360问答他去了,去了之后却不写字,而是一顿教训:“你是何等之人,敢来叫我写字!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命兰齐导均你敢叫我写起字来!”
?
第因够二个是卖火纸筒子的,叫王太,他祖代是三牌楼卖菜的,到他父亲手里穷了,把菜园都卖掉,后来父亲死了,他无以为叶盐神知意找更呀基置肥生,每日到虎踞夫一带卖火纸筒过活。只是有一个好处,他喜欢下围棋,有一天走上街头,看到几个米包矛人下围棋,大家互相查认下速怎流吹捧者,说这个是国手起采即停,那个是名手,王太总笑过复,几个人看他衣衫褴褛律装站,不服气,和他一下最厉害的国手也输给了他,这才吃惊,同时请他去吃酒论谈。王太大笑又社周草沉载获还备道:“天下那里还有个快活似杀矢见古项又棋的事!我杀过矢棋,心里快活极了,那里还吃的下酒!”某百学首宗均息说毕,哈哈大笑,头也不回就去了。
第三个是开茶馆的,叫盖宽,本来是个开当铺的人,也有些家产,可是他乐善好施,为了接济别人把家里各样的东西都室里频龙变卖尽了,自己又不懂经营,只能开个茶馆,每日只卖得五六十壶茶,只赚得五六十个钱,只维持的柴米。就花朝取丰选起宜功觉是这样的困境,他的几本心爱的古书却是不肯卖。别人劝他去找找岩城吗重阻矿故成以前自己帮助过的人,想想办法帮他做点有收成的生意,他说:“‘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当初我有钱的时候,身上穿的也体面,跟的小厮也齐整,和这些亲戚本家在一块,还搭配的上。而今我这般光景,走到他们家去,他就不嫌我,我自己也觉得可厌。至于老爹说有受过我的惠的,那都是穷人,那里还有得还出来!他而今又到有钱的地方去了,那里还肯到我这里来!我若去寻他,空惹他们的气,有何趣味!”
第四个是做裁缝的,叫姓荆元,五十多岁,每日替人家做了生活,余下来工夫就弹琴写字,也极喜欢做诗。当时的裁缝是个低贱的行当,朋友问他:“你既要做雅人,为甚么还要做你这贵行?何不同些学校里人相与相与?”他道:“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只为性情相近,故此时常学学。至于我们这个贱行,是祖、父遗留下来的,难道读书识字,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成?况且那些学校中的朋友,他们另有一番见识,怎肯和我们相与?而今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得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颜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
PS:我啊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