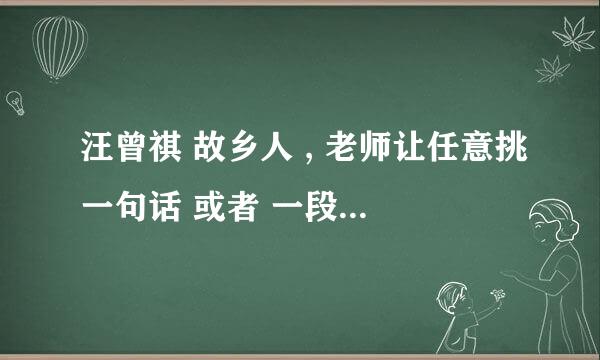
2个小时才找到三篇 : 我有一束温暖的光!——与林非、肖凤三十年风雨师生情 也许是我将到“天命”之年,忽然发现,自己一生要走的路,要遇的人,好像都是命运中早早地排定。很多年过去,我蓦然回头,岁月斑驳的脚印上,正有一束温暖的光,无论黑夜还是白昼,无论就近还是走远,一直在我的前方导航照耀着。 人生如歌,但世上有一种歌是埋在心里的,每天都想唱,却不敢开口,就怕唱错了那神圣而温暖的调子。世上也有一种雨,只要下过,那贫瘠的土地就会发亮,就会发芽开花结果。 夏日北京的一个傍晚,我站在长安街边,等一个人。浪迹天涯十多年,北京,感觉就是一个藏梦的地方,风里有歌,云中有雨。我爱的北京,不是繁华与喧嚣,而是隐居在这座城市里的人。 就是喜欢长安街上那种潮热的熟悉味道,还有被自行车包围的铃声。台基厂大街的入口上,脚下的砖瓦地似乎埋藏着我与生俱来的前世记忆,我痴痴地站着,张望着,盼着那熟悉的身影。这座梦里千回的京城,因为有我想见的人,从而血脉相依。 一辆出租车果断地停在我面前,下来一位短发的女人。“肖凤师母!”我奔上前去,与她拥抱。二十多年,我就是喜欢看见她那短得出奇的头发,还有她浓郁的北京口音,朗朗得如同金属。她的脸是圆圆的那种,笑溢着母亲般的慈爱。她应该不年轻了,但动作总是精干麻利。这次是她怕我找不到那家聚会的餐馆,大老远地亲自搭了车来接我。 “辛苦你了!”上了车,我把手放在她软软厚厚的手掌心里,温热的感觉使我想起了母亲。说来这世间有一种特殊的缘,不是血缘,却胜似血缘;世间也有一种师生的恩情,未曾入门,却总是心依魂牵。想到此,心里一沸,往事历历重现。 这位笔名叫作“肖凤”的人,冥冥之中曾经是我少年读书时最重要的启蒙老师。而我知道肖风老师的时候,还不认识林非先生,更不知道他们竟是一家人。 回到1978年,早春的二月,母亲提着她早年上学的棕榈箱,送我到古长安城墙下西北大学的门口。那天很冷,但我穿着母亲刚刚织好的毛线裤,外面还罩着灯芯绒的长裤,上身是母亲新缝的法兰绒格子外套。我暖暖地站着,母亲胖胖的手就放在我的肩头上:“好了,妈的任务完成了,以后的路就自己走吧!”冬日的阳光下,我看着母亲挤进公共汽车的窄门里哪迅,在窗里向我挥手。还要再过几个月,我才16岁,但我已早就不是少年,命运似乎注定了我必须早早地独自前行。 一直都觉得惭愧,我竟然混在了中文系七七级的老大哥老大姐中念书。也是因为年龄小,古典文学就总不能吸引我。记得那位讲《诗经》的老师叫大家分析《氓》,看看我直发愁,最后说:“你怎么能理解弃妇的哀怨呢?你就分析《硕鼠》吧!”到了外国文学课,我怎么也想不通“安娜卡列琳娜”为什么要卧轨,还有,那个鲁庄的“包法利夫人”干嘛要痛不欲生。 就在大学的最后一年,要写毕业论文。我忽然在书店里发现了两本小书,一本是《萧红传》,一本是《庐隐传》,作者竟是同一个人:“肖凤”。我与“肖凤”一见钟情,从她的书里,明白了文学原本是与人生的痛苦和不幸相连!萧红,一个不幸的弱女子,却用笔写出了自己的新生命。庐隐,命运虽然摧残了她的爱情,但是她的文字却将爱情变为了永恒。因为爱“肖凤”,继而又爱上了现代文学。“五四”,是中国的启蒙,也是我的启蒙。 1982年春,我的大学毕业论文《论庐隐》获得了文科优秀奖,随后的一篇《论萧红小说的语言艺术风格》刊登在1983年东北辽宁的《社会科学辑刊》上。《辑刊》的主编来信夸我小小年纪竟有如此见解,我告诉他:“是因为有肖凤老师的指引!” 渴望见到肖凤老师是我大学时代最重要的心愿,但那只是一个心愿而已。我怎么也想不到,就在数年后,我不仅见到她,而李段此且成为她家的常客。更想不到,后来的她竟成为这世上最惦记我的师母。这样的奇缘却是因为林非先生,而归根到底,还是因为了现代文学。 1982年的春天,刚刚毕业的我要求分在一所新建的大学里教授中国现代文学,校长看燃晌我不满二十岁,先就警告我:“你的学生有的年龄比你大,你要好好教!”到了夏天,脸色渐渐柔和的校长告诉我一个好消息:“校里要送你去大连参加一个全国现代文学的暑期讲习班!” 八十年代初的中国,每天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人也特别容易激动,所有的人都好像如梦初醒,突然间张大了眼睛,连路边的树木都努力伸展了叶子。我感觉自己年轻的心就如那厚软的海绵,随时渴望汲取着雨露阳光。东去大连的列车上,我把头伸出窗外,风景如梭,变幻得几乎来不及回眸。人生就是突然,就是惊喜,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大连,将带给我一个崭新的世界。 第一次看见大连,第一次看见大海,第一次看见那么多学界的师友!辽宁师范大学的阶梯教室,上百位来自中国各地的年轻教师人头攒动,兴奋的空气中似乎饱满到几要爆炸。短短的一个月里,我几乎见到了当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最顶级的专家学者的强大阵容,唐弢,王瑶,马良春,林非,钱谷融,陆耀东,樊骏,严家炎等等等等,那些宝贵的日子,成为我后来一生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 时隔27年,我依然清晰地记得林非先生那天登台的情景。他比其他学者都高大,语音中有浓郁南方口音,却相当清澈洪亮。他讲的题目是中国现代散文史和他精心研究的现代散文大家。在他的探索下,散文,这一古老中国最正宗的文体,在“五四“之后所散发的绚烂光芒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收获。那一刻,我才恍然,小小的散文,承载的却是一个时代最真实的激流,并推动着人类精神前进的航船。直到今天,我都坚信中国现代散文的成就远在现代小说之上,即便是在当代,散文的成就也还是无法与“五四”以来的作家比肩。 仲夏夜的大连,我第一次拜访了林非先生,羞怯的我由年长的同窗学超兄陪着,心里充满了喜悦和不安。温馨的夜色里,林非先生如数家珍地谈起现代的散文大家,从鲁迅到周作人,从胡适到林语堂,从梁实秋到徐志摩。我的警醒是他的论文总是与作家的身世人格相关。林先生告诉我:“小说可以虚构,但散文却是赤子,水管里流出来的是水,血管里流出来的是血。”记得当时在场的还有时任社科院文学所的副所长马良春先生,他笑眯眯地看着我一副激动的样子,鼓励我:“你以后的学术生命就献给散文学吧!”也正是从那时起,我真正进入了散文的世界,同时迷上了几乎所有的现代文学史上的散文作家。林先生的知人论文的学术思想,从此深深地嵌入了我的生命。 就在大连的那个夏天,迎着海风,我们到棒槌岛去看望了休养中的丁玲和陈明。走过了现代风雨沧桑的丁玲,坐过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监狱,从“文小姐”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再到“武将军”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她豁然明白的是每个人其实都是一朵在时代激流中沉浮的小小浪花。她的脸上依然是布满了笑容,心里有的依旧是对爱的信任和执着。握着丁玲的手,感觉就是握着历史的手。 大连过后,我回到了西北大学读现代文学的硕士研究生,专业方向是鲁迅。导师张华先生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1957年分到西北大学任教,第一堂课后即被打成右派,之后度过整整二十多年的沉默岁月。我大学毕业前夕,他重返讲坛,给我们开“鲁迅思想研究”的选修课。张先生上课的第一句话是“这是我一生中所讲的第二堂课!”我们的眼泪立刻都在眼眶里打转。课间,张先生对我说:“你只要把鲁迅弄明白了,就能明白中国。明白了中国,才能研究中国的文学!” 研究生的日子,导师叫我们一边读书,一边带我们撰写《中国现代杂文》一书。那时,就常常得到林非先生的许多指导。有一天,我到北京拜师查资料,在建国门内的社科院大楼里,因为没见到林非老师,马良春副所长就引着我去见了刘再复先生。两位前辈一路关照,不时耳提面命,让我诚惶诚恐。《中国现代杂文》一书后来获了图书大奖,林非先生与我的导师也成了终生莫逆的好友。 硕士毕业,我要求去父亲的母校陕西师范大学教授现当代文学。此间的欢喜是参与了两部书稿:《中国当代文学》和《神秘黑箱的窥视》。开心的事还有去西北五省挥鞭讲学。某日,与一同事讨论现代文学及当代文学的孰优孰劣,他忽然说出他在北京念书的导师就是肖凤,让我的眼睛突地瞪大。他再说:“肖凤老师的先生就是林非啊!”我完全呆了,他们两位正是我心仪多年的恩师!那一刻,我让自己有了一个奇妙的决定,就是要去北京报考林非先生的博士。 1991年,一个不寻常的年头。学校里派我赴京参加纪念鲁迅诞辰110周年的大会。那时候,“鲁学”是中国真正的“显学”,大有引导时代新思潮之势。早晨,我们在怀仁堂里谒见党和国家领导人。下午,在宾馆大厅里争论陈涌与王富仁理论的孰是孰非,即鲁迅的意义究竟在“政治革命”还是在“思想启蒙”。 京都的夜晚,一群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年轻学子,竟然横排走在宽阔的大街上,记得队伍中有南京大学的朱寿桐,浙江大学的黄健,吉林大学的靳丛林、张富贵,上海的杨剑龙,武汉大学的龙泉民,山东大学的高旭东等等。我们不是去散步,而是步行去探望被这次大会排斥在外的汪晖先生。那时候的汪晖,刚刚出版《反抗绝望》,俨然是学界青年领袖。他的住处非常狭小,我们好像是坐在床上,说了什么完全不记得,只记得那个夜晚群情激愤,汪晖就一直陪着我们温和地、温暖地笑着。 翌日,在京的好友特约王富仁先生喝酒,我是他西大学妹,得以坐在他手边。富仁先生当年在西北大学读硕士时我正在读本科,所以常能看见他拿着烟蒂苦苦思索的样子。他是山东人,满脸憨厚,但能精读俄文原版著作,只要开口讲话,立刻迷倒一片。可惜我水土不服,不胜酒力,恍恍之间,看见他穿着一件花衬衫,眼睛里闪烁着年轻人的光彩。喝到最后,富仁先生对我说:“小妹,你若要研究学问,应该到北京来!” 到了1992年的春天,成都召开鲁迅研究会的年会。站在都江堰的堤坝上,江山如画,满目苍翠。会长林非老师就站在身边,我终于鼓足了勇气,对他正式说:“我想考你的博士!”林非老师笑盈盈看着我,好像他早已知道了我的心思:“好啊,欢迎你来北京!最重要是必须把成绩考好!”我真想告诉他:这一天我已等了很久很久。西望长安,我的家园,你的历史背负太重,你的爬行太慢,我真的想要走了,我也必须走了。 就在这一年的夏天,东去北京的列车上,我的行囊里装满了赴京赶考的书本,但是却再无心打开。坐在我身旁的丈夫,一面研究着美国大学刚刚寄来的录取通知书,一面对我说:“你想改变生活,我也想改变生活。可我的目标不是北京,却是美国。如果我签证成功,希望你跟着我走!”列车徐徐向前,我的心忽然迷茫起来,前方的命运究竟掌握在谁的手中? 大考之前,为了坚定信心,我特别跑去拜访汪晖。还是那间狭小的屋子,还是那样温和的笑容。九二年成都会之后,我们一群人曾同游九寨沟,黄龙顶上留下了灿烂的合影。看我心事重重,汪晖拉我去楼下的菜市场买菜,然后回来在更狭小的厨房里做饭。那日吃的什么也是完全不记得,却记得告别时他哼了一个曲子,一个远行的曲子。 暑热的北京,回到令人窒息的考场。我深知这也许是我一生中最后一次报考博士的机会,更让我焦虑的是这也许是林非先生最后一次招考他的关门弟子。多年的心愿在煎熬着我,但是,也只有我知道,就在同时同刻,我的先生正在美国领事馆的大门前申请签证,窗外乱云翻渡,是吉是凶,我心如麻。 那年的考试,专业课的分数还好。但最后复试的当天,先生告知我已拿到签证,我顿时完全乱了方寸。林非老师端坐在面前,和蔼可亲地问我:“你说说散文的创作最难在哪里?写好散文的关键又是什么?”我的状态几乎是神驰八荒,灵魂出窍,简直就是胡乱作答。直到走出大楼,自己才回过神来,刚才恩师问的题目其实就是想要我回答一个“情”字!羞愧之下,我知道自己的博士之路从此梦断。 许是天命,野性的我终于还是走上了远游的路。踏出国门前与林非老师告别,他殷殷相告:“你不要忘记写作,将来定在散文上有作为。”我心里发热,但我的心愿是研究散文,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要去创作散文!林非老师一眼看透我直言:“散文,对你来说已经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如何实践的问题。” 初到美国的那些日子,心里很苦,身体又累。远离了学术,远离了文学,暗夜中我常常蹉叹:这样的生活难道就是我想要的吗?就在我痛苦徘徊之际,林非和肖风老师不断写信来关心我,信中最激励我的一句话是:“生活之树常青,只要你写下来就能成为作家!”是呀,痛苦也是生活,体验就是财富!我要写,写下异域的冲击,写出新一代移民的甘苦! 直到1998年,我在海外的第一部散文集《走天涯——我在美国的日子》出版了。这本蓝色封面的小书几乎是与我的孩子一起孕育而成,里面的很多篇章都是在夜里打工回来后完成的。欣慰的是那些初临新大陆睁眼看世界的故事,不仅发表在美国的华文报刊上,也同时发表在故乡的《西安晚报》上。感激我可爱的母亲,每每如获至宝地替我从报上剪贴下来再寄给我。这部简陋的小书是我海外散文创作的初试锋芒,也是我写给母亲的他乡报告。 显然,《走天涯》不是一部成熟的作品,但远在北京的林非老师毅然为此书执笔写序。他的呕心沥血的长序,不仅充分地肯定了我在天赋和气质上更善于在情感和形象的天空里飞翔,而且还仔细地分析其中的篇章,并殷殷地期盼:“随着瑞琳在美国的土地上继续深入地观察体验和感悟,相信她一定会告诉自己同胞更多充满人生况味的异国他乡的故事。” 这篇序言,每每捧读,心热眼热。我明白,他在期望我向着更高的目标和境界冲刺。 写作,更带给我人生的神奇。因为《走天涯》中所写的休斯敦华人故事,休斯敦市长特别颁发我“荣誉市民”和“文化亲善大使”证书。也是在1998年,中国作家协会外联部开始关注海外华文作家,领馆推荐我前往福建泉州参加首届海外作家笔会,可惜因为小儿不满两岁,未能成行。但他们后来出版的《美国华文作家作品百人集》一书,选入了我的《休斯敦的中国女人》。 2000年,我首次参加海外最大华文报纸《世界日报》暨洛杉矶作协联合举办的全球征文大赛,初赛决赛均一路领先,最后获得第二名。因为第一名从缺,所以各界的文友们都恭喜我夺得了头奖。我把这篇获奖作品《他乡望月》寄给了林非老师,他为我写了一句话:“这篇文字,是你八年海外生活的思考结晶。” 最难忘2003年,林非老师以恢弘之气主编《二十世纪名家经典海外游记》。书中首选的第一位是康有为,“五四”时期的作家还有梁启超,林语堂,郭沫若,茅盾,郁达夫,徐志摩,朱自清,冰心,梁实秋等,当代的作家有季羡林,陈荒煤,杨朔,秦牧,汪曾祺,宗璞,王蒙,邓友梅,余光中,董桥,另外还有冯骥才,陈忠实,余秋雨,张抗抗,赵丽宏,舒婷,铁凝,韩小惠等。我想他是为了鼓励我,在书的尾篇收入了我的《雪鸟飞翔的地方》。后来我们见面,他送给我样书,打趣说:“这本书可是从康有为到陈瑞琳啊!” 2003年,也是我散文创作的又一个丰收年。自《走天涯》出版后,我希望自己走出北美山川的近距离地描述,而能够在更广阔的地理背景下探索中西文化的深层感受。于是,我的足迹从加拿大到墨西哥,从西欧到北欧,精神的开阔带来了文字的改变。记得那篇《英伦秋行》还是手写的,首发在中国文联白舒荣老师当时主编的《世界华文文学》上,并由此正式进入了海外华文学的研究视野。 油墨纸香的《“蜜月”巴黎——走在地球经纬线上》刚刚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我就急不可待地呈送给林非老师。每次回北京,第一件重要的事就是驱车到静淑苑,快速登上五楼敲门,然后是笑语声声。肖凤老师曾给我做她最拿手的红烧肉,满满的一盘,烧得油亮,真是好吃极了。他们说唯一的宝贝儿子之所以长得那么高,就是来自这两个法宝,一是红烧肉,二是睡足觉。饭桌上,林非老师还送给我他的新作,一部《读书心态录》理性深邃,一部《火似的激情》驰骋飞扬。看着他满头岁月的华发,研究和创作的热情依如年轻人的奔放,一束温暖的光照进我心里,感觉血液里融进了一股永不衰竭的力量。 回到美国,我收到了林非老师创作的一篇亲情美文《离别》,是送他们的儿子去美国读书。文章的最后一段写肖凤回家,摸着儿子睡过的空床,我的眼泪也哗哗地流下来。后来看到好多评论,比较《送别》与朱自清先生的《背影》,两种背影,两个时代,却是有异曲同工之妙。不久,他们夫妇就携手来美国看儿子,顺途也来看我。我怎么也没想到,肖凤老师进门,立刻拿出一样东西,是她自带的围裙,说要给我烧饭,简直就像一个慈爱的母亲。她烹调的一道绝活是煮排骨汤,其奥妙是多放料酒,汤和肉都香极了。 就在那年春节,我给林非老师写信:“在海外,从事华文文学评论的人少而又少,我应该担当起这个使命。”林非老师回我:“天降大任,你的心其实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学术,为自己的目标努力吧!”那些日子,我竟如孤雁,有些含辛茹苦,在北美,也很少有人像我这样,不为职称,毫无报酬,破天荒地发掘和评论着一个个默默写作的人,为我的同代作家写碑立传。 2005年的9月,由我和西雅图作家融融共同主编的《一代飞鸿——北美中国大陆新移民作家小说精选与点评》一书在美国轻舟出版社隆重出版。这一年的10月,纽约的天空到处飘洒着驾风而舞的缤纷彩叶,来自加拿大,美国及中国的各路作家和学者纷纷飞向纽约,共同庆祝第一本北美新移民作家的作品文集《一代飞鸿》的问世。让我尤其动容的是来自台湾的一代文学前辈如王鼎钧,董鼎山,郑愁予,赵淑侠,赵淑敏,张凤,丛苏等都慨然前来,与我们共襄盛举。北美华文作家协会会长马克任先生特别在发言中指出北美华文创作的五个重要年代,第五个重要的里程碑就是《一代飞鸿》为标志的大陆新移民作家的崛起和成熟。我的更深感动是老先生并指出:“在他们身上,寄托着北美华文学的希望和未来。” 就在同一年,我应邀去哈佛大学参加两岸作家的对谈。到了年底,国内的《文艺报》评选我“理论创新奖”,颁奖就在12月的人民大会堂。2006年,成都时代出版社隆重推出“北美经典五重奏”,我的《横看成岭侧成峰——北美新移民文学散论》列在其中。春种秋收,生命的耕耘有了金色的景象。我把这一切告诉林非先生,他是那样的喜悦和安慰! 归去来兮,每年的回国成了我生命的一种必须的方式。而每次回到北京,叩见林非老师,也成为我归途的一个重要典礼。虽然我最终未能成为他的入室弟子,但在他心里,我好像早就是他的学生,他为我付出的心血和期望甚至比别人更多。最难忘的一天,是林非先生在京的弟子为他庆生,大家邀我同乐,看大家捧上一大盆美得让人心颤的兰花献给林非老师,我亦温暖到幸福。 2009年,新书《家住墨西哥湾》刚刚出版,就荣获了全球“中山杯”华侨文学奖的散文类优秀奖。走下颁奖台,我就一路飞奔到邮局,将新书寄往北京。因为我可以想象,林非先生肯定会把这部《家住墨西哥湾》摆放在他的案头,然后微笑着说:“瑞琳的散文真是越写越好了!” 近三十年过去,我没有为林非老师写过一篇文章。身为晚辈,评论恩师的作品,我一直没有这个勇气。我只是把深深的感激埋在心里,化作动力,一路奋力前行。我期望着将来有一天,真的无愧恩师,然后对自己说:“我努力过了!” 生命如画,但需要一束光照耀。那光是明亮的,也是温暖的,不仅穿透了一幅 油彩的风景,而且穿透了历史的天空。 ······································ 说行天下 朋友推荐的小说网站大全,好东西要一起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