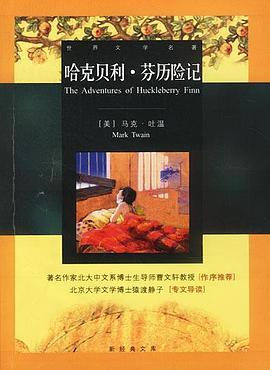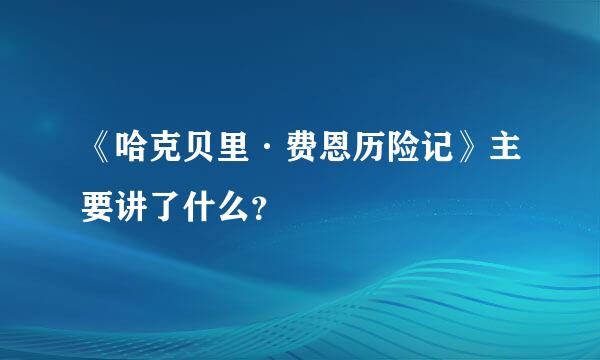
《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是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长篇小说代表作。这部小说中所描写的事情发生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前。作者通过一个名叫哈克的白人孩子帮助黑奴吉姆逃亡的故事,描绘了19世纪中叶美国中西部生活的各个侧面,揭露和讽刺了美国文明社会的丑恶现实,尤其对腐朽的蓄奴制度予以愤怒的谴责和批判。作品的思想倾向集中地体现在主人公哈克的身上。哈克从小就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儿,他没有受过文明的教化,不必到教堂去祈祷,也不必穿上体面的衣服,学那些文雅的举止。他喜欢独立的生活,本是个自由自在的孩子。后来,好心的道格拉斯寡妇收养了他,教他读书,送他进学校,一心想把他教成一个斯文体面,循规蹈矩的“模范”儿童,以便他将来能成为一个“文明人”。可是,哈克厌恶小市民呆滞的生活和虚伪的客套,他觉得日子过得“太闷气”,简直是“一天到晚活受罪”。他不断地逃学,还跑到树林里去睡觉,表示只要能“换换空气”,宁肯到“地狱”里去。对于世人所景仰的上流社会,哈克并不以为然。他非但不愿做体面的绅士,就是让他和“有身份的人”呆在一起,他也会觉得“浑身发痒”。他对周围的一切保持着一个纯洁的儿童所特有的好奇和敏感,凭着自己的亲身感受判断其正确与否,甚至对神圣的宗教信条他也提出了疑问:“要是一个人能祷告什么就有什么,那为什么犹肯·韦恩卖猪肉亏的钱赚不回来呢?为什么寡妇让人偷掉的银鼻烟盒儿求不回来呢?为什么华森小姐不能胖起来呢?不,我心想,祷告根本就没有什么道理。”哈克终于因为忍受不了死气沉沉的生活和文明的教化,从那个环境中逃了出来,去寻求自己理想中的自由生活。在马克·吐温笔下,哈克与这个呆板的社会规范格格不入,这才使得他免于被环境所败坏,保持了他淳朴、正直、善良的性格和清醒、敏感的头脑,出落得更加天真可爱。但是,作为一个在这样社会中长大的十二、三岁的孩子,他不可能不受环境的影响。作者如实地反映了哈克思想中的矛盾,更加强了这个人物的真实性——当哈克与吉姆相遇,并且和他乘着一只木排在密西西比河上逃亡时,他不得不面对当时严峻的社会道德问题——如何对待种族歧视和蓄奴制度的问题。这时,社会环境所强加给他幼小心灵的传统观念与他正直、善良的性格激烈地冲突起来。在这种激烈搜宴碧的思想斗争过程中,哈克的叛逆性格才真正成长起来。吉姆逃亡是为了躲避被卖到南方去的悲惨命运。当时,蓄奴制在美国南部占统治地位,这种统治比祥拿中部要残酷得多。在南方的种植园里,世举黑奴被当作牛马役使,即使是最强壮的劳力,经过七、八年的折磨,也就被榨干了血汗,凄惨地死去了。正如马克·吐温所说:“……无论对于我们白人,还是对于黑人来说,南方的农场都纯粹是地狱,再没有更温和的字眼可以形容它了。”正是出于怜悯和同情,哈克愿意帮助一个将要被抛进“地狱”的人去争取自由。可是起初他并没有把吉姆当作一个具有人的尊严的同伴来看待,他总是戏弄他,取笑他。后来,他发现吉姆善良,忠厚;对待自己有时象朋友那样诚恳,有时又象父亲那样关切;发现他“也跟白种人一样”,“惦记着自己的家里人”,和白种人一样具有作为一个真正的人的尊严。于是,哈克否定了社会灌输给他的种族偏见,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吉姆“倒是一个挺好的黑人哩”。有一次,因为恶作剧而受到吉姆的埋怨,哈克自觉惭愧,“简直恨不得去亲亲他的脚”。从此,哈克再也没有取笑吉姆,两人成了知心朋友。然而,在快到“自由州”的时候,蓄奴制的观念又开始一次次地折磨小哈克了。被他称作“良心”的那种东西在不时地警告他:拐走主人的财产是大逆不道。每当他听到吉姆为盼望自由而欢呼时,他就感到“浑身连发抖带发烧。”往日学校的教导也象瘟疫一样总是缠着他,老是有个什么东西对他说:“谁要是像你那样,干出拐逃黑人的事来,就得到阴间去下油锅。”在哈克面前,告发吉姆是一条符合上帝意旨的“正路”,而帮助他逃跑则是一条通向“地狱”的邪路。在这岔路口上,哈克战栗了。哈克的这种心理矛盾真实地反映了南北战争前奴隶制观念在一个善良孩子的心灵上所投下的阴影。马克·吐温就有过这样的亲身感受。马克·吐温6岁那年,他的父亲曾以地方法官的身份,参与对3个教唆奴隶北逃的废奴主义者的审判。当时有许多本地人在场,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威胁这3个白人,要把他们拉出去吊死。最后,在公众的欢呼声中,法官判处他们12年苦役。1895年吐温在他的札记中写道:“在过去那些奴隶制的日子里,全镇的人都赞许这一件事,那就是奴隶财产的不可侵犯的神圣性。帮助偷一匹马或一头牛是一桩低劣的罪行,而帮助一个被追捕的奴隶,……或是在有机会马上告发他时犹豫不决,则是一桩更卑鄙的罪行,那就带上了一个污点,一个洗刷不掉的污点。追捕奴隶的人持有这种观点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有可观的赏金;但是穷苦的人们持有这种观念,……而且是带着热烈的、不妥协的情绪,这是在我们久远的今天所不能理解的。那时,这种观念对我来说似乎理所当然;而且哈克……赞同它也是非常自然的,尽管在今天看来是那样荒唐。”不难看出,奴隶制度正是当时那个文明社会的基础,一个白人孩子要想从奴隶制偏见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将是多少困难。帮助一个黑奴争取自由意味着对社会的挑战,哈克必须拿出和自己的亲人、朋友以至于整个社会对抗的勇气来。哈克的思想斗争是相当痛苦的。他一度抵挡不住“良心”的谴责,给吉姆的主人华森小姐写了一封信,告发吉姆的行踪。可是,他马上又想起他和吉姆在木排上和谐、友爱的生活,想起吉姆对他的关怀和照顾,想起吉姆亲热地叫他“宝贝儿”,称他作“老吉姆在世界上最好的朋友”。这时哈克瞧着自己刚写完的那封信,感到非常不安,作者写道:这事真叫人左右为难。我把那张纸拾起来,拿在手里。我浑身哆喀起来了。因为我得打定主意,在两条路当中选定一条,永远不能翻悔,这是我看得很清楚的。‘我琢磨了一会儿,好象连气都不敢出似的,随后,才对自己说:“好吧,那么,下地狱就下地狱吧,”接着,我就一下子把它扯掉了。这标志着哈克和奴隶制观念的彻底决裂。他表示“从此以后就再也不打算改邪归正了。”他不愿再走文明世界的“正路”,不愿再做被人们普遍称道的“好事”,背叛了那个虚伪的“上帝”,选择了一条被当时社会所不齿的“邪路”。这条路实际上正是当时美国人民和资产阶级民主力量所走的反对蓄奴制的正义道路。它最后导致了1861年~1865年的南北战争——美国的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这个重大意义,小哈克当然是不可能了解的,但作者的用意却十分明显,他站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立场上谴责了奴隶制度。在两个逃亡者寻求自由的旅程中,哈克几次走进了密西西比河两岸的城市和乡村。这使他得以更广泛地接触社会,观察、认识那里所发生的一切。在这个游历的过程中,同样表现了他的叛逆性格。有一次,哈克在河上遇险,被格兰纪福家收留。在那里,他亲眼看到了格兰纪福和谢伯逊这两个大家族之间世代相传的血腥械斗。最后一次殴斗的直接原因是格兰纪福的女儿和谢伯逊的儿子私奔,结果,格兰纪福父子都在苦斗中凄惨地、毫无价值地死去了。作者在这里所描写的实际上是欧洲中世纪封建制度的残余,它发生在19世纪的美国,实在是对美国现代文明的一种讽刺。在这段经历中,哈克始终是一个旁观者,然而,却默默地表示出他对这种野蛮的社会现象的憎恶。哈克不能理解,这些高贵的名门世族、举止文明的绅士,为什么会无休止地互相残杀;当问起这世代宿怨的起因时,双方竟无一人记得。看到格兰纪福和谢伯逊两家人荷枪实弹地坐在教堂里听牧师讲“友爱”,听到他们热烈地谈论对上帝的虔诚,哈克感到讨厌,他想,“上教堂的人差不多都是万不得已才去的,(而进教堂乘凉的)猪可就不一样。”对于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爱情,那些高贵的绅士们都抱仇视、厌恶的态度,而哈克则不然。他无意中当了爱情的信使,听说这对情人在夜里逃走,并且已经过河脱险,他感到由衷的高兴。哈克的这些思想与世俗观念是背道而驰的。“国王”和“公爵”是哈克路遇的两个骗子。他们唯利是图,一路上不择手段地谋取金钱,甚至冒充玛丽小姐的叔叔,想要夺取她应分的遗产。他们靠着信口胡说,痛哭流涕,骗取了人们的信任,得到了一口袋价值6000块的金元,还拍卖了原主人所有的产业和奴隶。对金钱抱着贪婪欲望的不只是这两个骗子,还包括市镇上几乎所有的人。当“国王”和“公爵”把一袋金元拿到公众面前时,“大伙儿都冲着桌子跟前围拢过来”,“人人都瞧着眼馋,直舔舌头。”马克·吐温在这里揭露了美国文明的一个最突出的特征——拜金狂。但唯独哈克是例外,他蔑视文明世界天经地义的公理。在小说的第4章里,就有一段描写哈克把自己的钱无偿地送给萨契尔法官的情节。后来看到两个骗子如此无耻,贪婪,他说:“我一辈子也没见过象国王这么贪得无厌的家伙,他简直是什么都要吞掉才甘心。”这时,哈克已经不只是怀着厌恶的心情冷眼旁观,而是勇敢地站出来,救助孤弱者。他从“国王”和“公爵”屋里偷出了钱袋,使它物归原主;还向玛丽小姐揭露了这两个家伙的本来面目,并机智地安排了惩罚他们的计策。哈克的旅程确实是一种“历险”。他一次又一次地怀着厌恶或恐惧的心情摆脱那个凶险、丑恶的现实世界。在小说的结尾,哈克说:我觉得我只好比他们俩先溜到印江人那边去,因为莎莉阿姨打算收我做干儿子、让我受教化,这个我可受不了。我早就尝过这个滋味了。这个含蓄的尾声暗示了哈克同美国传统观念的决裂。和哈克一样,马克·吐温厌恶当时的社会,同时又对自由理想的实现抱有一线希望。他曾经在哈克和吉姆的旅程中为他们安排了一个幻想中的自由州卡罗,但是,他也知道,这种希望很渺茫,因此让他们安排在迷雾之中漂过了卡罗,始终没能找到这个幻想中的乐园。作者这样的处理是明智的,他自己在现实中没有看到一条通向自由的道路,也没有牵强地为他的小主人公指示这样的道路,于是便有了哈克性格中的适世主义倾向——哈克对现实社会的叛逆只能最终表现为消极的逃避,无可奈何的隐匿,而不是有力的反抗。值得注意的是,吐温把自然与社会相对立,并以这样的观点来批判现实。比起《汤姆·索亚历险记》来,《哈克贝利·费思历险记》揭露社会更具有深度和广度;但就作者手中批判现实的武器来说,还依然如故。他没有力图从哈克的社会经历中寻找哈克性格形成的根本原因,而是把儿童们自然的天性——淳朴、善良、渴望自由、追求美好生活的天性与扼杀这一天性的文明社会加以对照,强调他本身的个性尚未被丑恶的环境所败坏,把他摆脱奴隶制偏见的原因也归结于“健全的心灵”战胜了“被毒害的良心”。同样,作者把文明世界——实际上也就是资本主义现实世界——的本质解释为社会对大自然粗暴的败坏,社会道德对人们善良本性粗暴的败坏。因此,作者以浪漫的、抒情的笔调描绘密西西比河上的自然风光和哈克同吉姆在木排上清新和谐的生活——它象征着自由。同时,他又以讽刺的、漫画式的笔触描写密西西比河两岸人们的粗野、残忍、虚伪和贪婪——它代表着文明社会。这种鲜明的对照固然使现实社会更显得丑恶,使作者理想的主人公更显得可爱,却也使哈克的形象带上了一些超脱现实的色彩。在哈克的形象塑造上,马克·吐温采用了多种艺术手法,其中有些是极有特色的。例如,作品的构思很有独到之处、吐温继承了传奇式流浪汉小说的传统,让哈克扮演一个天真无邪、对文明世界非常陌生的孩子,让他走进这个世界,一路漂泊,用一种孩子所特有的好奇、天真的眼光观察这个世界,怀着一种对周围的一切并不理解的心情游历这个世界。这样一来,既可以通过孩子天真的眼睛折射出来的景象,微妙地表现作者对那个世界的讽刺和批判,又可以反映主人公如何在游历的过程中逐渐熟悉那个世界,认识那个世界。有的美国评论家把这称作“导向觉醒的富有教育意义的旅行,”实际上这也就是哈克叛逆性格的自然的成熟和发展过程。作者善于运用对比、衬托的艺术手法来刻画人物,而且重视人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小说中的两个最重要的人物——哈克和吉姆。是两个有着共同的追求自由的理想,而又具有不同性格、不同肤色、不同年龄、不同经历的角色,他们之间的这种异同,使得各自的性格显得更加鲜明。有了老吉姆的忠厚、诚恳、慈爱,才更烘托出小哈克的天真、淘气和善良,有了吉姆同哈克的友谊及吉姆的高尚人格对哈克的感染,才使得哈克对种族偏见的反抗更显得合情合理,真切动人。哈克的好朋友汤姆在书中是个次要角色,但是他对于哈克性格的塑造来说却是十分有意义的。他也是个善良、机智的孩子,与哈克不同的是,他读游侠小说入了迷,一心想要脱离社会现实,去追求书中惊险的英雄生活。汤姆的这种吉诃德式的幻想,正衬托出哈克的桑乔式的清醒。这两个人物在《汤姆·索亚历险记》中都出现过,对比之下,汤姆正是《汤姆·索亚》中的小汤姆,而哈克则在广泛接触社会之后成长起来了。他的思想更不受束缚,更实际,他不仅违反了传统的道德观念,而且对书本中的神圣信条也发生了怀疑。这部小说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写法,全书以主人公哈克自述的口气写成。哈克一本正经地把故事讲给读者听,还不断地谈着自一己的感受,这样一来,他的性格就不仅是在他所经历的一系列事件中,而且还在他本人的叙述中细致、传神地表现出来了。哈克讲故事所用的语言正符合他这个乡村孩子的身份,字句间透着质朴、幽默,充满生动的口语和粗俗的俚语,没有一点矫揉造作的痕迹,而且极富表现力。就象哈克的性格与文明社会格格不入一样,他的语言也大大触犯了文明、优雅的规范,闻其声,知其人,用这种“叛逆式”的语言来塑造这个不接受教化的小叛逆者的形象是再合适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