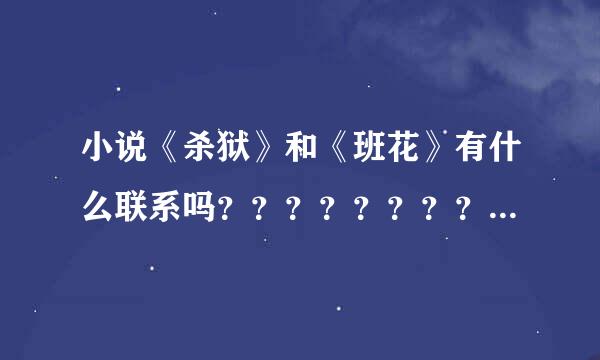家父不久就去世了直到去世也再没说放不下书桌。我为父亲地遗体洗梳整理家母说他这辈也没这么慈和过。我的父亲安静地躺在床上他终于安静了下来他那颗一生都在浮躁与狂暴跳动的心脏确实像我母亲说的我父亲从没这样慈和罩困过他甚至在微笑但那并不是我收拾出来的功劳是他最后终于学会了微笑。
我很平静我妈也很平静生关死劫这数年看了多少?
我问我母亲“妈我以前问过爹一句话。我问他有没有为我骄傲。”
我的母亲看着我的父亲我知道平静归平静她的心灵和生命也随着那个厮守一生的人去了。 我母亲说“去打仗之前问的吧?你刚走他就说了。仗打完了我们才知道你去了打仗。”
“爹怎么说?”
“你爹说每时每刻。”
我轻轻亲吻了父亲宁静的额头。我走了出去拿起了扫帚地上又有了落我弯下腰开始扫地。我直起了腰我的手和我的脸像南天门之上的树皮我已入耄耋我已经十岁了。我直起来腰我看着远处云雾缭绕的南天门。我再没跟人说起但我一直像我的团长那样想着山巅上缭绕不散的云雾是三千人的灵魂。
地扫完了我拿起菜篮零钱用塑料袋装着我身体还好虽瘸却也用不上拐杖只是老家伙的动作总是很慢。这院就是迷龙跟他老婆和他们家的小崽以前住的房现在住满了人我的孙在曾经是迷龙住的房间窗口拿小野果扔我我捡了起来假装咬了一口然后做出一张酸掉了牙的老脸只是我已经没牙可掉他笑得很开心。
我十了扫完地我就得去买菜这个点才能买到便宜菜。家母早已与家父在地下团聚狗肉也在它十四岁那年走了后来我有了一个家我有了工作后来我退了休我的孩又有了孩我孩的孩又有了孩这样很好老头就是看着小孩高兴。
唠叨完了我就得去买菜。我去买菜。我蹲在桥头的那些菜担边挑着小菜。没哪个菜贩会喜欢这样一种挑选法的他们唠唠叨叨地说我就装作没有听见。要过桥才能买到便宜菜。我过了桥桥是虞啸卿最早盖的后来翻盖了。我讨着价还着价我看见南天门想不想看见它我都得看见南天门。
刚下的菜很新鲜我得回家得趁新鲜让它们进锅里。我起身我走人今天又有小小的胜利我买到了又新鲜又便宜的蔬菜。
一辆车堵在桥头司机在鸣着喇叭车很引人注目因为它半个车厢里堆满了花圈空着的半个车厢有一张椅和一个老头还有两个被迫陪他坐车厢的陪同。我抬起头看见物首念一百岁的虞啸卿。他还是那样一百岁了还是那么有身份。我不晓得他从哪里来的但就那些陪同看起来他蛮有身份。
每一个花圈上都写了名字最大也离他最近的一个写着我那团长的名字旁边贴了两条我一生愧对的挚友我必须面对的挚友。我低着头从他的脚下走过我听着他正在那里急切地向他的陪同者发问“真找不到一个人了吗?找不到一个我认识的人了吗?”我走着脸上便泛起笑意。我抬起头那笑意已经绽开我尽力让它抹平让它平和。
我很想笑我不想笑老头笑起来不好看。我们都有了各自要回的家现在我要回家做饭。于是我与那辆车渐离渐远我回家做饭。
扩展资料:
我的团长我的团内容简介:
抗战末期,一群溃败下来的国民党士兵聚集在西南小镇禅达的收容所里,他们被几年来国土渐次沦丧弄得毫无斗志,只想苟且偷生。而日本人此时已经逼近国界,打算切断中国与外界的联系。
收容所里聚集了各色人物:孟烦了、迷龙、不辣、郝兽医芹轮、阿译等等。他们混日子,他们不愿面对自己内心存有的梦,那就是再跟日本人打一仗,打败日本人。因为他们已经不抱有任何希望了。他们活得像人渣,活着跟死了也差不多。
师长虞啸卿出现了,他要重建川军团。但真正燃起这群人斗志的是嬉笑怒骂、不惜使用下三滥手段的龙文章。龙文章成了他们的团长,让这群人渣重燃斗志,变成勇于赴死之人。
这些人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的命运就是炮灰的命运,他们面对的是一场几乎必死无疑的战争。 这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对得起“中国远征军”这五个字的中国远征军题材的小说。
列宁在评价高尔基的《母亲》时说:“这是一本及时的书。”今时今日,在尤其需要我们对未来抱有信心的时候,本书也当得起这一评价。